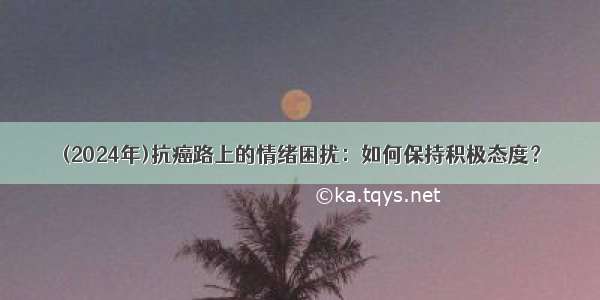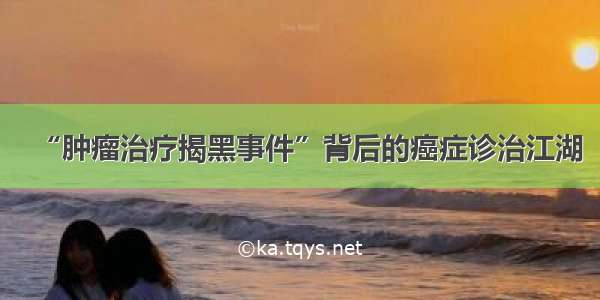
在各种肿瘤治疗新药
新疗法层出不穷的今天
只有先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
才能保障医生在超指南
超适应证治疗时的自由度
从而最终保障患者的权益
肿瘤治疗黑幕调查
4月18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化疗科主治医师张煜发表了《写给我挚爱的国家和众多的肿瘤患者及家属——请与我一起呼吁,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一文。
文章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巍给患者做不必要的NGS基因测序、开不合适化疗方案药物,以及推荐无效、昂贵、不合法的NK治疗等一系列行为,致使患者花费增加十倍却更早死亡。一如张煜在文中所恳求的,这件事很快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4月19日,国家卫健委回应称,对于有关情况和反映的问题开展调查,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不到一天时间,“医生反映肿瘤治疗黑幕”的消息已经在网上炸开锅,“肿瘤治疗”这个医学问题被拿到大众面前讨论。对此,北京一位知名消化肿瘤内科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医学的专业性,决定了医患处于信息不对等的两端,专业医学问题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解释清楚。但通过这次事件,应该要讨论一种更为科学的监督管理体系或制度。只有先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才能保障医生在超指南治疗时的自由度,从而最终来保障患者的权益。
被滥用的NGS检测,狂飙突进的产业
家住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的马进仓就是张煜在文中提到的“花费增加十倍却更早死亡”的患者。他第一次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就诊时,就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同时有肝部继发性恶性肿瘤、淋巴继发性恶性肿瘤、高甘油三酯血症、鞘膜积液等。因为已经有转移癌,消化科医生建议不用做手术了,直接转到肿瘤科做化疗。
由于不信任当地医院,马进仓没有选择直接化疗,而是转而先后求助于北京三甲医院和民间偏方。他们这趟坎坷求医旅程的最后一站是上海。在马进仓外甥的推荐下,一家人于7月2日来到了上海新华医院普外科医生陆巍的面前。双方第一次见面的一个实质性结果,就是陆巍让马进仓做了NGS基因测序,理由是“为了避免无效治疗”。
NGS基因测序即高通量测序,或称为下一代测序。前后,随着精准医学概念的兴起,检测技术的成熟及成本的下降,高通量测序开始被应用于肿瘤治疗过程中的诊断,并成为一个增长迅猛的新兴产业。据前瞻产业研究院行业报告,~,中国基因测序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在30%以上。从至,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年会每年以NGS基因检测为主题的远程会议占比已经由约10%提升至约70%。根据的一份报告,当时预测在五年内,中国肿瘤NGS检测市场规模可达500亿~1000亿元。
华大基因肿瘤事业部总经理朱师达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过去的两种基因测序技术,只能测定单个基因突变,与之相比,高通量测序能同时测定数百个乃至更多基因,为靶向药物、免疫治疗提供更全面的参考信息。用于检测的样本主要有肿瘤组织或血液两种。
马进仓做的是抽血检测。他的女儿马荣对此回忆说,陆巍说,基因检测是为了更快找到化疗药,“当时他没说做穿刺,也没说可以取组织做检测,我以为只是抽血就能完成”。
这正是张煜文中对陆巍的质疑之一。在张煜看来,相比之下,抽血做的NGS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按常规应将患者诊断时使用的胃镜病理组织切片检测更准确。张煜还称,目前临床工作中发现NGS测序对于化疗药物敏感性极其不准确,只能用来筛选靶向药物。尤其对胃癌,抽血进行NGS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在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胃癌临床实践指南中,这种“液体活检”更多在疾病进展而难以取得肿瘤组织样本患者中使用,在中国临床肿瘤协会版胃癌诊疗指南中,将其列为第3类、最低水平的证据。
对此,陆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患者来的时候是胃癌多发肝转移,还吃了一个月麝香。“应该是肿瘤没控制住,腹痛厉害,疼痛6~8级,不能进食,影响睡眠”,患者不愿意再做胃镜活检,他也不能强制。
北京某三甲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NGS检查用在偏晚期病人身上合适一些,不同瘤种也有不一样要求。通常面对患者时,要先取组织做病理,再根据患者经济条件,决定是否做NGS。NGS对于靶向药物选取、免疫治疗有着更大的价值,“一般在临床中使用化疗药物时,我们不完全遵循NGS的检测结果,参考意义比较小”。而在拿不到组织、不适合穿刺时,可以用抽血方式替代,“但要提前和患者说明,抽血准确率不如检测组织”。
即便通过测序发现基因突变,也未必直接能指导肿瘤救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在两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她的患者中有80%都会拿着基因检测报告来就医,其中有人会带着好几本检测报告,但这些报告在消化道肿瘤领域临床价值很小。“非小细胞肺癌、淋巴瘤、乳腺癌都有特定的基因突变,但胃肠肿瘤没有,基因突变导致癌症的相关性还没有被充分证实,二代测序对于未知肿瘤还在研究阶段”。
长期观察医疗行业发展的医库软件科技董事长涂宏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利益的推动下,中国NGS肿瘤检测存在严重滥用现象。
一名骨癌晚期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NGS检测血和组织的另一大区别还在于费用。据国内某基因检测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正因血液中肿瘤细胞DNA较少,DNA片段浓度比组织中低,开展测血业务时,需要检测数据量会更大,采用技术会更复杂,“所以在成本和价格上也会比检测组织更高。价格会高50%左右”。据《财新》报道称,在营销人员动辄以血检“无痛”等噱头的推动下,国内肿瘤用药基因检测行业中,选择血检的患者大约占到九成。
涂宏钢说,开展NGS肿瘤检测业务的前提是具备医学检验资质和具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试剂盒。但除了初,原国家卫计委批复的26家肿瘤诊断与治疗NGS技术应用试点单位外,目前,国家层面尚没有专门针对NGS检测的准入机制和监管体系,“处于市场充分竞争的时代”,整体准入门槛偏下。近几年,国内一些医院和第三方外检公司形成了共建实验室模式,即企业给医院提供技术设备、检测试剂,医院负责检测收费,但整个市场仍以外送为主。
马进仓接受的NGS检测就属于外送,但却显得不那么正规。据马荣回忆,在与陆巍的第一次见面时,一个自称“吴经理”的人匆匆赶来,把马荣叫到楼梯安全出口,站在窗口前拿出POS机,刷走了马荣18600元。随后,一个实习护士抽了马进仓两管血,被“吴经理”用塑料袋装走,送往一家名为上海艾汭得的第三方基因检测公司。
朱师达指出,各个检测机构提供的报告解读都依托于自建数据库与系统,“基因检测的分析解读是一个复杂的判断过程,依赖于前期数据的积累和技术层面的能力”。这意味着采样、检测、分析解读都可能出现结果偏差。
前述北京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曾将一份样品送检两家基因检测公司,得出彼此矛盾的结果。起,国家卫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每年开展肿瘤诊断与治疗NGS室间质评,由实验室自主报名参加。,全国有146个实验室参加质评,126家实验室回报结果,满分53家,满分通过率仅为42%。
前述基因检测公司相关负责人就指出,这一行业企业尚缺乏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一些企业虽营收不断增高,但亏损连年扩大。燃石医学的招股书显示,至第一季度,公司分别净亏损1.31亿元、1.77亿元、1.69亿元和5257万元。另一家业内知名的肿瘤基因检测企业——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招股书则显示,截至、、末,公司产生的净亏损分别是4.2亿元、4.6亿元和6.76亿元。涂宏钢也表示,肿瘤用药基因检测行业通常会给医生30%的回扣。在行业发展初期,因产品同质化严重、投入大等因素,普遍处于融资、砸钱、营销、亏损的恶性循环中,最终代价转嫁到消费者即患者头上。
治疗不规范与超适应证用药的一线之隔
马荣还记得,陆巍在第一次见面时说,你父亲的病情挺严重,治愈是不可能的,但按照我的方案,活三年没问题,努努力,把生存期延长到五年,或者六年。但陆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却表示:“(马进仓)的病基本上是AFP(甲胎蛋白)阳性胃癌,多发肝转移,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病期非常晚,预期生存期1~3个月。”
去年7月13日,马进仓的血液版NGS检测报告出炉,包括807个基因。根据报告,陆巍给马进仓制定的首个化疗方案是“一线治疗方案FOLFOX”,即氟尿嘧啶与奥沙利铂联合用药。
这版方案真的需要如此多的基因信息做参考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某大三甲医院胃肠肿瘤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常情况下,胃癌一线化疗前看三个必检项目就够了,即影像学、病理学与HER2基因检测,单查HER2这一项免疫组费用不高,通常在100元~200元。
马荣不记得父亲是否单独做过HER2检测,也看不懂这份长达68页的检测报告。就在收到结果两天后,7月15日,陆巍告诉马荣,他因马进仓住院时间太长而被投诉,并介绍他们去一家名为中大肿瘤医院的民营医院,进行第一次化疗。公开报道显示,上海中大肿瘤医院的最终控制人之一游凤开或为莆田县前云村人。
陆巍表示,前2个周期的治疗对症状控制有效,患者能吃得下、睡得着了。但是血AFP持续升高1万多(注:正常人血清AFP含量≤25ug/L,肝癌患者AFP会显著增高。),经过重新评估,陆巍称,他给患者提供了4个建议:一是继续原方案,密切观察;二是放弃化疗,回家进行支持治疗;三是换指南中的后线方案;第四,采用个体化方案。“当时详细和一直陪在患者身边的家属谈了后续治疗。家属表示患者年轻,愿意尝试个体化方案治疗。所以才有那个推荐的药物,参考了这个疾病的中英文文献和药物原理,以及NGS结果。”陆巍说。
这份“个体化方案”正是引爆舆论的其中一个争议点。前述北京一位消化肿瘤内科专家介绍说,AFP阳性胃癌是一种临床上比较罕见的胃恶性肿瘤,与普通胃癌相比,AFP阳性胃癌的肝转移率、淋巴结转移率更高,且预后更差。更为棘手的是,“目前针对甲胎蛋白阳性的晚期胃癌,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可供参考的明确指南。”他说。
前述北京消化肿瘤内科专家说,“医生内部对这个方案也有比较大的争议,但他所有用药,都在文献中找到了依据。医学专业方面的问题,还是等待国家卫健委来统一发布。”
国内一家顶级肿瘤专科医院的一位肿瘤内科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药新用、超适应证使用,在临床中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情,处在一个灰色地带。有些病人如果不是超适应证用药,可能也活不下来。
在没有明确指南的情况下,医生该如何正确开展超适应证治疗?前述上海肠胃肿瘤专家指出,不能因AFP阳性胃癌没有明确的用药指南,就自己独创用药方案,应该以普通胃癌治疗指南如《(CSCO)胃癌诊疗指南》、大型临床研究结果、药品说明书等作为用药指导原则。如果医生想做超适应证用药的临床研究,则要有详细的试验计划和方案,事先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反”。
世界肺癌大会主席、广东省人民医院终身主任吴一龙接受《医师报》采访时表示,卫健委开始牵头制定了《新型抗肿瘤药物合理应用的指导原则》,其中明确地规定了抗肿瘤药物在适应证内用药和特殊情况下用药的问题,特殊情况下用药,不能称之为超适应证用药。要坚决反对的超适应证用药是那些证据级别不强、只凭动物实验或Ⅰ期临床试验,就给患者应用的情况。
9月1日,河南郑州市,河南省肿瘤医院旁的一家“共享厨房”,每到饭点就会有大批癌症患者的家属来这里做饭。他们大多因为看病家庭负担较重,为了节省花销,也为了病患吃的干净、放心些,便选自己动手做饭。图/IC
中科院院士、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在4月27日的卫健委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超适应证的药物使用和超治疗指南的临床研究,应在临床药理机构和伦理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下开展。
还值得指出的是,陆巍并非肿瘤专科医生,而是普外科医生。美国并不允许外科医生进行内科治疗,但在国内,由于没有相关法规,外科医生做内科治疗、外科开展肿瘤化疗等现象并不罕见。另有医生表示,外科医生不能主导内科治疗方案,作为传统主导肿瘤治疗的医生,外科医生习惯性手写一些方案做参考,是可以理解的,但最终内科方案应由多学科会诊决定。
被张煜“点名”的,还有抗肿瘤明星药物PD-1抑制剂的滥用问题。张煜在文中写到,有医生滥用PD-1抑制剂,在胃癌术后、胰腺癌术后、肠癌术后、胆管癌术后的明确不需要进行PD-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错误的告知患者可以明显增加疗效,从而诱导这些患者进行PD-1抑制剂治疗。
PD-1的使用是有禁忌症的。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教授黄岩等人今年3月在《中国医学论坛报》上发文强调:PD-1单抗不是万金油,进入了医保并不意味着可以乱用,它也不是对化疗等传统肿瘤治疗的替代,医生需要根据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情况来为患者选择用药,也要根据病人的个体情况制订精准化治疗方案。
张煜还多次发文称,“有一部分医生喜欢更改标准治疗方案”“造成患者的经济花费增加、毒副反应增加,甚至死亡率升高”。张煜指出,“很多抗肿瘤药物本身非常好,却被一些医生甚至三甲医院医生滥用。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两方面:一是专业知识不足,一是经济利益所致。”
“在外地转诊到北京求医的患者中,治疗方案未完全按照指南走的情况,确实很普遍,这是中国医疗水平不均质导致的。”前述北京乳腺肿瘤内科医生解释说,北上广的大型综合医院与国际领先医疗水平不相上下,站在这个高度看地方医院给出的用药方案,难免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与当地医疗水平、医生知识储备和经验都有关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就在《医师报》上坦言,“不能完全否定张煜医生的观点”,他表示,治疗不规范确实是目前中国医疗领域最大的问题,肿瘤领域尤其如此。马军建议,从医疗机构来看,肿瘤治疗应该分层次进行,建议超适应证和超范围治疗在国内的一些具备科研能力、承担定向课题的大型医院才可以开展,而地市级以下医院应该遵循基本规范化的治疗原则。
魏则西死后,细胞疗法仍在江湖行走
在马进仓接受第二版化疗方案后,陆巍又跟马荣说:“一开始,努努力,加一个NK细胞治疗,对他来说,恢复更好,更容易产生效果,特别是他自己免疫力不足、对肿瘤消化比较差的时候。”
NK细胞疗法,这听起来很炫很高科技,以至于让马荣当时不得不把陆巍打来的电话录下来,以便自己事后重听以更好理解,但如果她知道这跟当年魏则西接受的DC-CIK细胞疗法原理如出一辙,可能就不会同意接受治疗了。
一名単亲妈妈在医院门口支起了理发摊,以便照顾住院的27岁白血病儿子。
无论是NK还是DC-CIK,都是将健康人或患者自身免疫细胞取出后,经体外扩增回输至患者体内,以达到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抗癌的目的。在众多的细胞免疫疗法中,马进仓所接受的NK细胞疗法并非目前最主流的一种,但的确是“外面宣传最厉害的”,北京某三甲医院曾负责细胞治疗的医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原因在于,NK操作最简单。”
它的操作流程是:从患者体内抽血,在实验室培养扩增,14天后将更多的NK细胞回输进人体。听起来,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大招”,但到目前,细胞免疫疗法仍然只是一种辅助疗法。这是因为,随着癌症的发展,NK细胞在体内增殖的能力和持久性是有限的。而且,NK细胞存在于人体的外周血中,几乎难以到达肿瘤产生的部位,这也是细胞免疫疗法当下的普遍困境,多年来都没有解决。
尽管陆巍究竟有没有向患者一家推荐NK疗法,双方目前仍各执一词,但为马进仓打NK针的公司上海嘉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以兵,已经成为这次事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身影。
工商资料显示,陆巍在之前曾是嘉慷的股东之一,但陆巍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和徐以兵一开始在校友聚会时认识,后来和他的公司在CTC(循环肿瘤细胞)检测上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先后两次转过徐以兵1万元,但这是科研合同款。《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事以电话和邮件的形式联系徐以兵,均未成功。
如果觉得《“肿瘤治疗揭黑事件”背后的癌症诊治江湖》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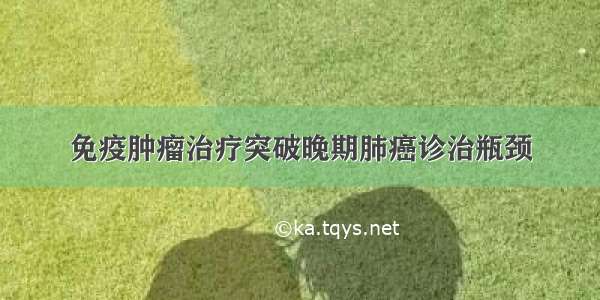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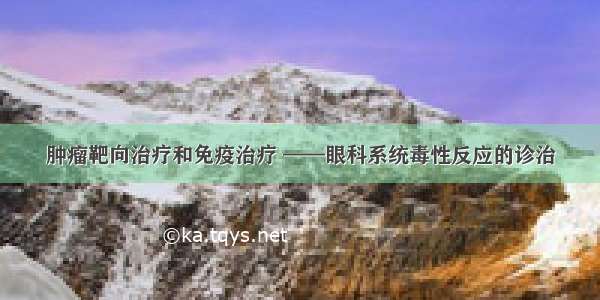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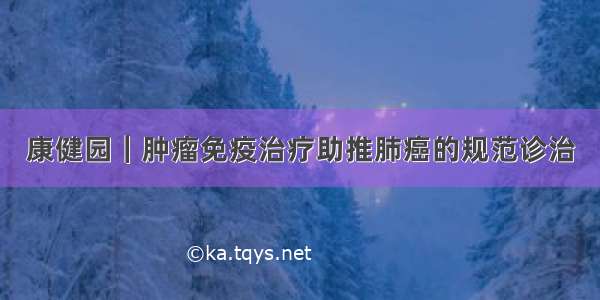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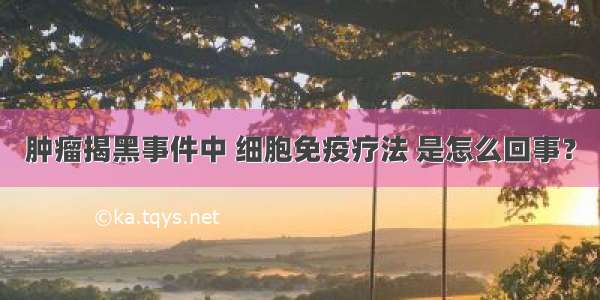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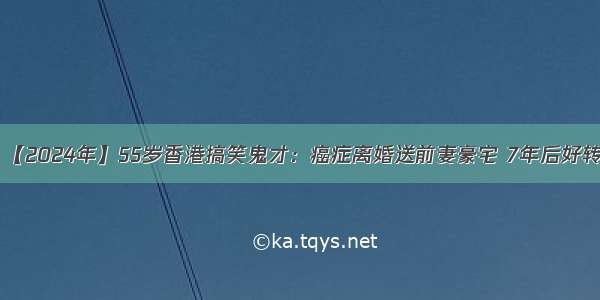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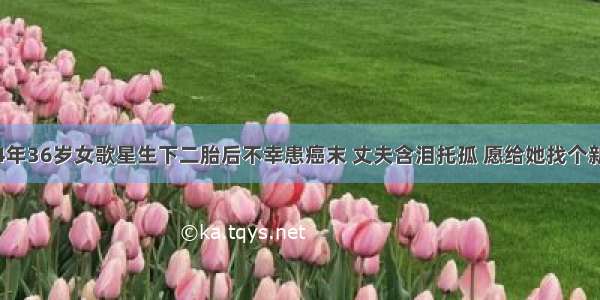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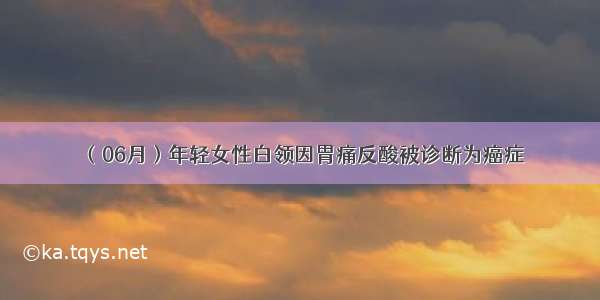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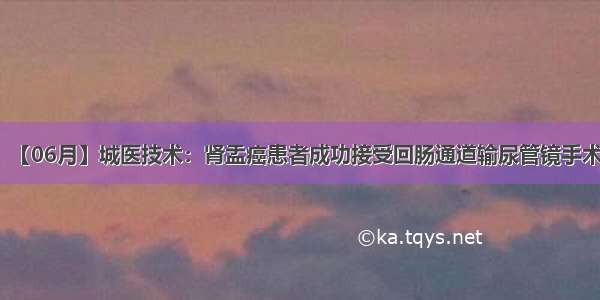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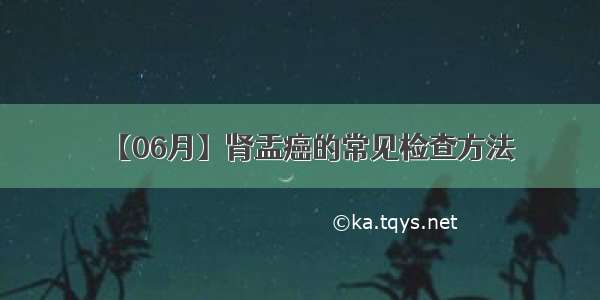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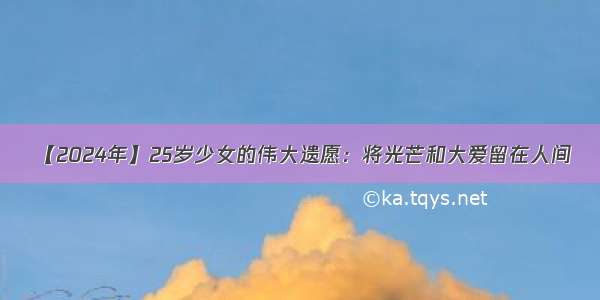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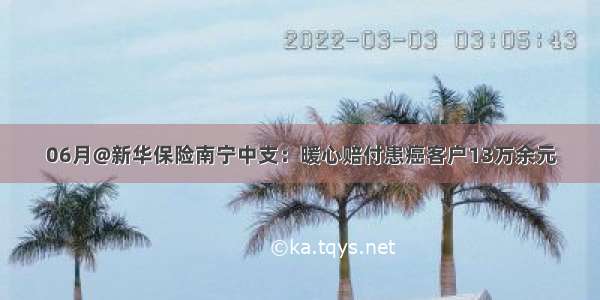
![[2024年]患癌奋斗的陈奕迅:再次捧红的一首歌 鲜为人知的故事](https://ka.tqys.net/uploadfile/img/2024/06/02/a7a275dd427756b477f2e0c2dc6472e2.jpg)
![[2024年]HAOEYOU:深入探讨子宫内膜癌的精准医疗](https://ka.tqys.net/uploadfile/img/2024/06/02/1ae39012b197eade1f4dc2579d4c27f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