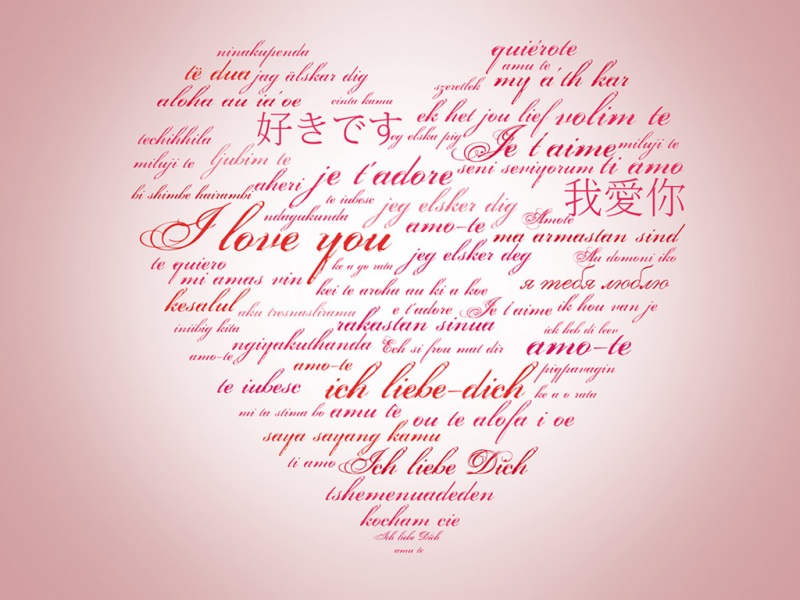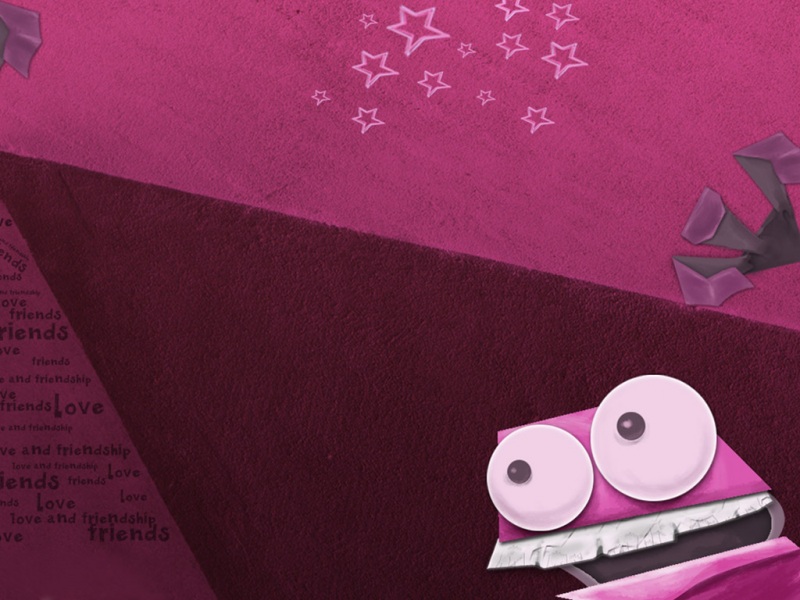“我是上海图书馆培养出来的,进上图那年十几岁,还像个孩子。”1944年出生的赵嘉福指向后排家人的位置,“比我两个外孙女现在的年纪还小。”
赵嘉福1961年进入上图,从事古籍书画修复装裱、碑刻传拓等工作,经手修复大量古籍善本、名人尺牍、碑帖拓片、民国舆图、盛宣怀档案等,并参与众多国家重大修复项目,包括国家图书馆善本《赵城金藏》、明代《西厢记》,嘉定太仓古墓出土古籍,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受损古籍等珍贵文献。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修复师生涯中,赵嘉福带领团队抢修了大批饱含中华民族宝贵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的文献资料,令众多命悬一线的历史文献“起死回生”。
今天(8日)上午,上海图书馆为赵嘉福举办古籍修复从业六十周年座谈会,“当时做这个工作,用上海话说,哪能想到会噶红?过去是默默无闻的。怎么坚持60年?可能今天说起来有些落伍,那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当初学这门技艺,完全没有名利思想,安排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但要做,还要做好。”
一旁,赵嘉福的夫人、同样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姚卫笑他:“坐了50年冷板凳。坐热了,你的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光辉也在座。起,赵嘉福受聘担任该院首批特聘教授。在此之前已因肺癌动了一次大手术的他任教不到一年,再次因病动手术,仅仅调养半年,又回到了学校。赵嘉福说,从事这一行一辈子,有责任把手上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年轻人。
从二胡手到修古籍的人
赵嘉福是上海人,小时候喜欢音乐,1960年初中毕业,考进上海民族乐团拉二胡。三年困难时期,文艺单位压缩编制。1961年,他面临转岗。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上海博物馆,一是上海图书馆。这一年,赵嘉福17岁,对两家单位了解不多,以为到博物馆是当讲解员,到图书馆就是处理借还书。因为普通话不好,他自觉无法胜任讲解员的工作,于是进了上图,被分配到古籍修复小组,这才知道图书馆不单是借书还书。
古籍修复行当由来已久,以往主要存在于民间书画装裱作坊。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图书馆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文献公藏机构之一,汇集了一大批古籍修复名家,包括古籍修复大师曹有福、碑刻传拓圣手黄怀觉,古籍版本学名家潘景郑、瞿凤起等,可谓卧虎藏龙。
在全国业界,赵嘉福以掌握古籍修复、碑刻传拓、碑帖书画装裱等技艺之全面而闻名,碑刻传拓尤其擅长,他的师父就是黄怀觉。“我跟黄先生学习,是传统师父带徒弟的模式。刚开始学习,师父给了两把刀,先磨几个月刀,哪天师父看你刀磨得不错,允许你帮他磨刀了,那才是认可了。师父干活的时候,在旁边看,打下手、递工具,然后自己再慢慢上手。反复模仿、揣摩师父的手法、刻碑的节奏,甚至声音。到最后关着门,我在里面刻碑,外边人听声音、节奏都跟师父一样。这就算可以了。”
“我受这些老先生的影响很大。”赵嘉福一直感念上图老馆长顾廷龙的知遇之恩。除了学习古籍修复专业技术,顾廷龙馆长还特别注意培育年轻人的文化修养,亲自教他们写毛笔字,并请馆里的潘景郑、瞿凤起两位老专家轮流授课,讲古代汉语,教版本目录。
1964年,中央图博文物局面向古籍修复人才开培训班,赵嘉福得以跟随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先生学习了两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古籍修复、碑刻传拓的“南派”代表人物即上海图书馆的曹有福、黄怀觉,北派的代表人物正是北京图书馆的张士达,被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称为“国手”。赵嘉福则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专家,南派、北派的古籍修复技艺在他的心中、手中糅合。用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的话来说,“从北京归来,赵嘉福就成为当时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的当家小生”。
除了修复古籍,赵嘉福还在上海各地留下了众多石刻作品。碑刻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并非机械地将书法作品复制到石碑上,而是要在篆刻过程中体现出原作的精神气韵,需要刻碑者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与艺术理解力。每次接到碑刻任务,赵嘉福反复揣摩原稿,力求百分百还原原作的笔势、艺术特征。
碑刻也是一门艰辛的室外长期作业。赵嘉福带领团队冒着严寒酷暑,顶着石灰粉尘,在刻刀敲击岩石的叮叮声响中,创作了一块又一块蕴含着上海文化精神、纪念意义的石刻作品。如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革命英雄纪念碑、华东师大碑、顾廷龙书沈钧儒生平碑、邹容墓志铭“革命军中马前卒”、徐光启的碑廊、以及由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写的“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世纪大道”“上海市民主党派大厦”等,累计上百块,成为上海一道新时代的文化景观。
“上世纪80年代,赵老师来嘉定刻碑,不仅分文不取,都是自己坐公交车来的。”原嘉定博物馆文保部主任、赵嘉福的学生金蓉回忆。华东师大有一块“大师石”,石长10.8米,高3.2米,重110吨,正面刻“师大”二字,也可读作“大师”,落成时是上海最大的独体石刻,亦出自赵嘉福之手。“这么大的石刻,阴刻好还是阳刻好?赵大师想出了‘不阴不阳’的刻法,先阳刻再四面勾印。这是大家没见过的刻法。”周德明说。
从师徒相授到多种培养模式
,上海图书馆“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赵嘉福被确定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赵嘉福从业的近60年,背后正是新中国古籍修复事业发展历程的缩影。“从小生到老生再到新生。”周德明如此概括。
“赵嘉福的手也曾挑过担、挖过土,开过防空洞,那段时间也是古籍修复的低潮期。”即便是在那段“角落里的时期”,赵嘉福始终没有放弃这门手艺。1989年,文化部图书馆司委托上图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面向全国招生。赵嘉福担任培训班主讲老师,由上图指派参加培训班的张品芳、邢跃华拜赵嘉福为师,由此成为该馆最后通过师徒相授习得技艺的古籍修复师,也就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上图的“第三代”古籍修复从业者。
53岁的张品芳如今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也是全国不多见的能独立完成从篆刻到传拓和拓片修复的专家,与古籍已经打了30多年交道。
她所带领的团队则是更年轻的上图“第四代”。其中年龄最小的王欣出生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届硕士毕业生,去年入职上图。
座谈会上,众人为她究竟该算第几代“争”了起来。如果按赵嘉福授业,年轻的王欣似乎与张品芳、邢跃华算得上“平辈”。杨光辉则补充,“品芳主任也帮我们带学生。我们的学生到了上图,也是品芳的学生带。”
“在学校的两年,基本上是学理论知识。要真正上手、独立‘上路’,可能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本科学理,因为对古籍修复的兴趣“改行”的王欣说。
模糊的“第几代”背后,是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赵嘉福说,过去大学里没有古籍修复这个专业,现在很多院校开设了专业,不仅培养本科、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点。“像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北师大、天津师大、辽宁大学、中科院等,现在都动起来了。”
“为什么要设古籍修复的专业硕士乃至博士点?”杨光辉直言,一些中大专院校也有相关人才的培养,“但往往学生并不知道自己修的是什么,很难对自己手里的事业培养起责任和感情。我们希望培养不光会古籍修复,也懂书的人才。”
赵嘉福补充:“从事古籍修复,看不懂文言文不行。上图从顾廷龙馆长时代起,从来就不是单纯培养技术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句读,版本要能搞清楚。”他至今记得当时修复明代《西厢记》,“午休时,我就读《西厢记》,张生跳墙的情节,太有趣了。”
周德明所说的“新生期”,是国家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古籍修复保护日益得到重视。一方面是大量亟待修复的古籍,另一方面是当时全国不足百人的修复力量。作为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古籍书画修复装裱、碑刻传拓大师,赵嘉福担任起大量教学任务。每次全国碑刻传拓培训班在各地举办,赵嘉福都作为特邀导师。他每年长驻辽宁、重庆两地的古籍修复传习中心,为当地培养古籍修复与碑拓行业的新生力量。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后,赵嘉福成为研究院特聘教授。
6月,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并在湖北、重庆、上海等6个省、直辖市成立传习所。,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复旦大学传习所揭牌。经过5年学习,传习所第一批学员明天(9日)下午将接受包括赵嘉福在内的专家考核,正式“出师”。
面向社会招生、重视“口传心授”的传习所,与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结合,形成了目前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两条腿”模式。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已有三届、30多位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硕士毕业生,其中半数进入相关机构。“流失的一半,非常遗憾。有些学生希望留在本地,但本地可能提供不了那么多相关岗位。”杨光辉透露,复旦正在筹备建立“纸质文物修复医院”,希望培养“书籍医生”“艺术品医生”,为全世界的纸质文物和艺术品提供服务。“上海正在构建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修复保护力量加入,是一个很大的支撑。”
“古籍修复不是一家、一个单位的事,而是整个国家和人类文明需要传承的事业。”这是赵嘉福和众多古籍保护从业者的共识。
栏目主编:施晨露
本文作者:施晨露
文字编辑:施晨露
如果觉得《身患癌症两次手术仍在复旦育新人 新中国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赵嘉福的60年》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